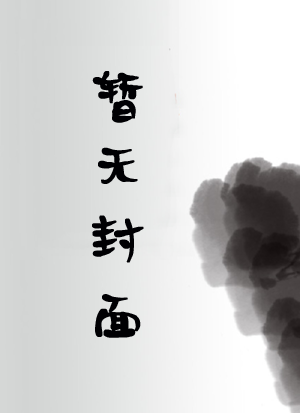宋縣令身為一縣父母官,事務繁雜,不能多待,第二日便啟程回了平陽縣。
他來的時候裝了半車禮,走得時候帶回的禮,隻多不少。
金婆婆把東西裝好後,清荷最後拿出一個小包袱,遞給宋縣令:“宋哥,巧巧的生辰快到了,這裡頭是我給她的生辰禮,你記得交給巧巧。”
宋巧巧的生日在臘月二十七,剛好過年那幾天,平陽縣太遠,清荷不方便去,每年都是備好禮物送過去。
提起女兒,宋縣令笑得寵溺,嘴上卻道:“妹子也太寵她,一個小姑娘家家的過什麼生辰。”
“那不行,巧巧不能白叫我一聲姨啊。”宋巧巧長得好看,又乖巧懂事,小小年紀,知書達理,清荷稀罕得不得了。
縣裡還有公務,宋縣令不便多耽擱,他與周家人一一道别後,便坐馬車回了平陽縣。
等宋縣令走後,村裡其他人才從王長喜一家嘴裡,知道縣令老爺來過他們村子。
一個個又懊悔又驕傲,懊悔的是沒見到縣令大人長什麼模樣,但縣令大人來過村裡這一條,也足夠他們驕傲的。
虧得王長喜不知道苗不離也是官,否則大夥估計會把沒見到宋縣令的這份遺憾,轉到苗不離身上,把他當猴看。
周家多了幾個人,大夥都以為是周家的什麼遠親。
苗不離長得幹幹瘦瘦的,精神頭倒是不錯,宋縣令回縣衙後,他整天就帶着老仆姚水生在村裡轉悠,至于姚立則被他打發出去砍柴了。
用他的話說,在周家吃住,總得幫周家做些事,他和我姚水生年紀大一點,身體跟不上,把事情都交給姚立最合适。
時間一晃而過,很快到了臘月二十五。
眼看就要過年,韓忠、周清波、劉廣林三人前幾日就從府城回來了,周家的作坊昨日也停了工。
清荷跟女工們說,要年後初八才開工,叫大夥好好休息休息,過年期間工錢照發。
不管是作坊的女工還是送貨收菜的車隊,都是一樣的,可以休息十幾天,不僅不會少工錢,還有過年福利。
這可把給周家做工的村民高興壞了,就沒聽說過這樣的好事,不做工也有錢拿。
哪怕今天作坊沒有開工,作坊外的空地上還是熱鬧非凡,甚至比平日裡人更多。
因為今天周家要給工人發過年福利,啥叫過年福利,大夥都不明白,一個個好奇得很。
年前沒事,村裡聽到消息的人,都擠着來看熱鬧。
等到了作坊外,看見擺在外頭的兩扇大肥豬,一堆布匹,還有一筐用油紙包好的東西,村裡人眼都看直了。
“這就是過年福利?瞧那兩扇大肥豬,膘真夠厚的。”
“還有布,還是細棉布,那一包包的是糖吧?”
“我的娘哎!都是實打實的好東西,周家對自己的工人也太大方了。”
一群人對着作坊前的東西議論紛紛,家裡有在周家做工的,臉上多了幾分期待,沒有的,則是滿臉羨慕。
這其中壯壯爺爺奶奶顯得尤為高興,他們家兒子媳婦都在周家做工呢,這什麼福利能得兩份呢。
鄉下人過日子講究實在,要說什麼最實在,那自然是吃穿二字,因此清荷準備的福利也頗為接地氣。
每人五斤豬肉,一匹布,一包白糖,一包糕點,都是實實在在的好東西。
為了發福利,周明遠在村裡買了一頭肥豬,就是王長喜家的那頭。
因着女工每日可以拿一些紅薯渣和不要的菜皮菜葉回家,王長喜家的兩頭豬養得特别肥。
當然也不止王長喜家的豬養得肥,那些女工家裡養的豬,就沒有不肥的。
作坊裡的女工加送貨的車隊,再有譚玉嬌和黃秀才兩名夫子,這些人加起來,一共有二十二個人。
既然是福利,就得讓大家滿意,清荷特意請了張屠戶來,讓大夥自己選肉。
想吃肥的就割肥的,想吃瘦的就割瘦的,喜歡吃排骨的,就砍排骨,五斤肉抵七斤排骨,絕不讓大夥吃虧。
最後剩下豬頭,下水什麼的,清荷家自己處理。
作坊的工人拿了東西,都不忘給清荷道一聲謝謝東家,而清荷也會回上一句“辛苦了”。
領了東西的工人心裡美滋滋,臉上喜洋洋,正要拿着東西回家,又被清荷叫住。
“大夥拿了東西先别急着走啊,福利還沒完呢,作坊剛開工的時候,我就說過,隻要大家好好幹,過年我給大家發大紅包。”
“現在我叫誰,誰就上來拿紅包啊,頭一個就是我們的趙管事。”
被叫到的趙慧趙管事,頂着衆人的目光走到清荷面前,清荷遞給她一個紅封,又說了幾句鼓勵的話。
“接下來是胡春桃。”
胡春桃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,她也有?
可是她才去作坊這麼短的時間,東家竟也給她準備了?
胡春桃暈乎乎地走到清荷面前,村裡人這才注意到,不知在什麼時候,大夥口中的苦命女人,早已變了模樣。
不再是一副苦相,不再是一副怯弱瑟縮模樣,取而代之的是挺直的背脊,堅毅的眼神,宛如一株生命力頑強的蒲草。
一個接一個的員工領走紅封,這些紅封裡,多則五兩,少則一兩,是根據每個人的表現來評定的。
黃秀才捏着手裡的紅封,隻覺得掌心發燙,那裡頭是五兩銀子,周家姑娘說他教學教得好,這是給他的獎勵。
而他猜測,是周姑娘知道他想要去參加秋闱,變着法子的給他送銀子。
罷了,就是現在還回去,周姑娘也不一定會承認,這份恩情,他記下了。
将銀子裝在兇口,黃秀才等清荷忙完了,才走上前去跟她告别:“周姑娘,在下今日就要同母親回鄉過年了,明年再見,先提前祝姑娘過年好。”
如今已是臘月二十五,再不走,回去該忙不過來了。
“夫子一定要回鄉嗎?天這麼冷,你和于大娘幹脆别回去了,就留在村裡一塊過年吧。”黃夫子對村裡的孩子和作坊的男工都很負責,清荷挺感激他的。
黃秀才微微一笑:“族中還有長輩,若不回去,恐落人口實,過完年我會盡快趕回來。”
這話裡的暗藏意思,清荷聽明白了,怕是黃秀才族中也不是一片和諧,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
既是這樣,她也不好挽留,便與黃秀才提前道了别:“黃夫子一路順風,明年再見。”